再次的,童偉格在所有人面前招喚了屬於他的獨門幻術。是屬於時間的,卻也不合時宜;又或者正因如此不合時宜而如此契合時代。
翻開書頁,童偉格深情寫著杜斯妥也夫斯基、契訶夫、聖艾修伯里、卡夫卡、莫爾、卡謬、沙林傑、蒙田,甚至傅柯、班雅明…,但其實每一字句都俯拾為他自身文學世界的明暗調焦與音準對位。他展示了如何沈靜閱讀書寫,如何思考,意思是,如何將一整個宇宙「童偉格化」的精準過程。這是從最細微的感覺出發,以獨具的感性天賦仔細調校文字,在世界中旋出一個獨特且堅實無誤切片的寫作。
童偉格以文字與這些作者共構一個「感性分享」的獨一世界,他為他們說情就像是與知己性命與共。其實,這便是執哲學意義核心的友誼。童偉格的小說或許比任何他的同代作家更接近一種「精神小說」(noofiction)或「大腦小說」,當我們閱讀時,我們與他那些質樸安靜的字句一起封印於特屬於他風格的文學時空之中,彷彿終於可以在時間暫停之地覓得居所,而且每當我們再翻開書頁,這恆久的文學世界總是如常地在書裡等待著我們,「在一個相對較為和善的世界裡重逢」,因此安心。
童偉格小說裡的世界一逕古老而新鮮,是還只有老人與小孩的開初,像一切童話故事的開場與結尾,一老一小長久地佇立曠野,剪影透亮而乾淨。然而,以「童話故事」為書名的這次卻不無弔詭,成年的「他」進場,我們驚喜發現,原來「他」是一個極高明獨到的讀者。蘊含在這本書背後的是一個完整的存有視域,一種至為純摯明亮的文學之愛。
童偉格愈是書寫其他創作者就愈是書寫自我與自我書寫,他的書屬於一個所有已被寫就的過去與尚未書寫的未來都已回返自身的世界。因為永恆回歸,所以一切傷害,即將降臨的與已經降臨的,皆療癒。對童偉格的有效評論註定只能是這個永恆回歸的再次回返,因此,也再度療癒。
童偉格總是沈默而安靜,在他的靜默中,已然停擺的世界被再度擲往未來,每個文字都同時響起怦然心跳。生命的巨大苦難與夭折是童偉格世界的「先過去式」,這是一切文字進場前便已盤據紙面的生命基底。是的,傷害與死滅命運的不可改變,單是這個事實就足以讓所有人心肝摧折面如死灰,然而,童偉格安靜地坐在書桌前,書寫的可能始於療癒的已經完成。正是在「已經」與「早就」的巨大時差中,在不可能跨越的生死坎陷裡,童偉格像靜默的聖徒持續寫著他的世界之書。
因為,童偉格寫道:「靜默而專程的奮鬥,是一個人在臨時居所裡,唯一能做的不下流之事。」安靜,恆久,同時觸碰神的領域與存有的純淨底蘊。在這本書裡我們再度返回未來必定只能以「童偉格」命名的這個文學之夢。
台灣中生代作家駱以軍早年常被評為淫猥,中年以後作品愈見溫暖,二人都有著「後傷害悠長時光中的巨大溫柔」。童偉格不是駱以軍式的花腔女高音,但無疑的在情感的溫潤質樸上卻渾然天成,綿密的文字封印一整個令人心安的宇宙。雖然有心碎與死亡,然而即使亡靈與逝者都在那個明亮純淨的夢中世界裡撫慰著我們。
對時間的細微知覺來自因純淨而顯露的真實感官,這是童偉格的「感覺的邏輯」,時間因此成為書寫反覆摺曲的溫柔物事,像是織錦般在書頁裡閃閃發光,這是一個迥然不同的時間切片,「一個以自身光照作為模糊範圍的孤島」。
書中討論的作者無疑地經過童偉格的嚴格挑選,14篇長文成為繞經這些作者(與他們巨大的文學內在共振)回返自身的悠長文字旅程,其中,〈偏遠的應答〉執掌樞紐之鑰,童偉格這麼開場:「也許真的,真正的閱讀是重讀 …」,然後,「我們確實可以將任何時代的小說作者,同等復原成比較素樸的面貌」。還原宇宙成一個不花俏、不下流但卻「複眼」觀看的素樸面貌,而這必然是「對我而言」的風格化觀點,是「我」對我私心喜愛作者的動人說情。那麼,首先是唐吉訶徳,「在悖反的語境中,他變成他的世界裡,惟一具有古典格調的,那樣一個真正跟『命定性』對抗的悲劇英雄。這是因為在他的世界裡,只有他孤身一人,如此認真地相信逝去時代的價值觀:他癡愚而執著地相信,一個逝去的世界,依然可以在一次簡單的出門漫遊中,由他孤身一人尋回。」然後是契訶夫,「關於自己的文學實踐,契訶夫終生無意解釋清楚的,或根本無法自我定義清楚的,正是他在複寫的,那個已然停擺的世界…在那樣的世界裡,不是他們心裡想的什麼令人哀傷,而是不管他們怎麼做,在這個地方,在他們介入這個世界之前,世界基本上好像真的已經細緻到只剩虛空的徒勞了。」
童偉格悄然挪移於塞萬堤斯、契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等作者之間,他流變為他們,但首先是因為這些作者亦反身流變為童偉格。似乎沒有人能比童偉格更理解他自己,文學既怪異又本份地從事一種由自身出發並回返自身的複式摺曲運動,這是一種自我對自我、自我回返自我、自我尾隨自我的巴洛克迴圈與疊層。童偉格為那些作者說情,為他們篩撿還原一個「比較素樸的面貌」,但究極而言,這個面貌亦正是他自身,一個多重映射的鏡像,文學積體中一逕豐饒茂密的劇中劇。這或許正是評論童偉格作品的難題:一個嚴密回返自身的作品,所有評論僅以自動成為此獨特迴圈的外圍而有效,去指出(或其實是「再指出」)作品不只一次透過各個被援引作者或故事光景所已經述說的內在風景。
閱讀亦總是我們的重讀,我們繞經童偉格回返左拉,只因為左拉亦同時在此旅程中舒展開顯成童偉格的素樸文學景觀,一種絕對安靜卻鮮活的靜物畫(still life)。或問,何以是左拉?又何以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納博科夫或其他作者?毫不需要故做高深的理由,蒙田(童偉格援引的作者之一)早已代所有的這種友誼回答,很有名:「因為是他,因為是我」。
這是由寫書的絕對靜默所開啟,浸潤「兩者之間」的溫柔光照,以整體文字證成「善待他者」的纖細共感與共存,以及以特異之眼穿透文學積體所重新激活的小說活體。童偉格以其一逕謙遜的文字向我們展示一種逼近存有論高度的友誼,一種僅由書寫所舖展的alter ego,阿甘本這麼寫道:「在我意識到我的存在何其溫暖之際,我的感覺即被一種共感所穿越並將其偏移與帶離到朋友,朝向另一相同。友誼就是這個自我最親密感覺核心中的去主體化作用。」(Giorgio Agamben, L'Amitié)
文學在此成為對於存有溫暖的共同感受,成為因友誼而明晰透亮的純淨內向經驗。因為童偉格,他人不再是地獄,而我,不再能等同於他者。在《童話故事》所綰起的明亮結界裡,人透過文學分享著存有的溫暖,書寫提升到一種存有論的高度,成為「存有的感覺本身」。
「那就像是」,童偉格最後寫道,「當你將球擲出之時,你同時也已在一個十分偏遠的地方,預見球的歸返。」
愛童偉格意味著愛文學。而文學,已是一個安靜抽長成存有溫暖感覺的廣袤結界。
2014/02 《印刻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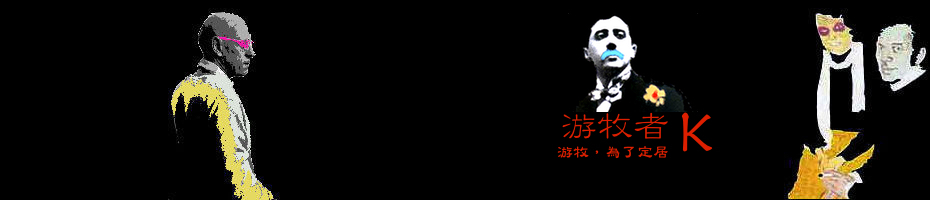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